
南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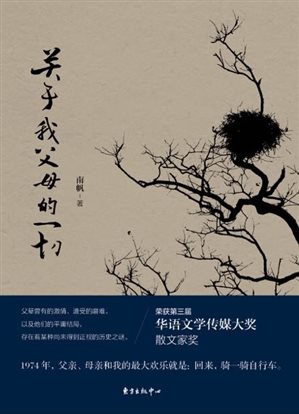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南帆 着 东方出版中心 2016.11
1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一书写于2003年。我曾经在序言之中说明,这本书是一个早产儿。它打乱了我的写作计划,自作主张地挤到前面来。当时,种种记忆、感慨和叹息烤灼得我坐立不安,如同反反复复的噩梦。所以,写作毋宁是摆脱不尽的缠绕。一吐为快,喘出一口气,然后才能干些别的事情。完稿之后转过脸来,日子的确轻松多了。
如同某种刻意的回避,这么多年我不再翻阅这本书。我熟悉这本书的封面,暗红的底色上套印父母的黑白照片;我很少打开封面,背后的文字保存了写作时的伤感与内心疼痛,我不愿意再陷进去。我几乎不向外人提起这本书,不是再三催讨决计不送。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一个文学奖。我在颁奖会的致词之中坦率地表示,对于这本书没有太多的自信。一个儿子置身斗室思念父母,竭力猜想历史为什么捉弄他们,这一切对于公众具有多少意义?这本书确实敞开了内心,从各种感叹、忆念、想象到迷惑和悔恨。这恐怕也是我不愿示人的一个潜在原因。我习惯于冷却文字,隐藏强烈的表情,做一个反讽式的分析家而不是夸张的抒情诗人。为什么不增添一些缠绵情话或者兴高采烈的笑声?为什么不敢当众舞蹈或者公开流泪?我的内向性格大部分要追溯至生活的训练。无拘无束地暴露自己,收获的多半是伤害——如果说,这仅仅是我屡试不爽的小经验,那么,对于父亲说来,这恐怕是刻骨铭心的重大挫折了。一次坦诚的交代与一生的蹉跎,这即是父亲贡献给这本书的情节。父亲一辈子的心得就是小心翼翼的提防技术,他尽职尽责地将这一笔精神财产传给我。所以,戒意植入了神经,即使写作的时候可能忘情地倾囊而出。一些人半小时之后就可以向陌生的面孔倾诉自己的失恋或者五年之内的晋升计划,这种爽朗的性格令人羡慕。无数宠爱簇拥在他们周围,阴谋和圈套闻所未闻。但是,我做不到,甚至充当听众也会有些不自在。大多数时候,伤感与内心疼痛是说给自己听的,写作犹如独白。所以,出版社邀请重新出版《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犹豫——有必要吗?
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些段落还是让我心酸难抑,眼角湿润。我抬眼看了看窗外刺眼的午后阳光,放弃了修订或者补充的念头。一个完整的写作心境留在了当年,重新介入有些唐突。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巧合:我写作这本书的年龄,正是父亲结束下放生涯返回这个城市的年龄。
我曾经有一个心愿:到母亲的灵位前烧一本书,算是一个告慰。我还想请母亲宽心,她这一辈子已经竭尽全力,各种磨难不如说是历史悲剧分配的一个个细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逃脱不了。不过,这件事迟迟没有做——仿佛又觉得有些多余。母亲一辈子仅仅操心几个亲人,阴差阳错,厄运连连,她甚至连喘气的间隙也没有;现在,她终于甩下了那些揪心不已的事情,何必还要拿什么历史不历史打扰她的安宁呢?
2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出版至今的这一段时间里,书中提到的祖父那一幢老宅子拆除了。
拆除之前,那一幢老宅子已经朽烂不堪。门框破损,柱子开裂,潮湿的地板一寸一寸地腐烂,大厅的瓦顶塌了一大片,几缕刺眼的亮光从瓦片之间的窟窿照射下来。老宅子的大限来临之前,大部分窗棂、柱础、门板已经被陆续缷下来卖掉。那一天铲车进场,轻轻挥了挥铁臂,老宅子就轰地一声坍塌为一地的瓦砾。
我的童年记忆之中,每年正月的某一天都要跟随父母到祖父的老宅子来。老宅子隐在一条幽暗的巷子深处。巷子的石板路面湿漉漉的,好像从来没有干过;巷子的两旁多半是二层楼的木板房,不时就有一条竹竿横过巷子上空,竹竿上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物。据说这条巷子曾经是这个城市最为繁闹的商业区。祖父老宅子是一个三进大院落,天井由大石条铺成,两个八角形的大鱼缸,一盘石磨,一口水井,井水冰凉刺骨。天井的边上是一个小花厅,两层的木板房。花厅里还有一个小院落,院子中央的石板撬起了两块,堆上泥土种一架的葡萄。正月的天气多半阴冷难耐,这种四面透风的老宅子几乎呆不住。父母和叔叔、姑姑到祖父祖母的房间里谈天,我会伺机溜上花厅的二楼,二楼走廊的木栅栏边上晒得到太阳。现在回想起来,每年正月的这一天就是家族的聚会的日子了。
很长的时间里,我从未意识到“家族”这个词与我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一只背囊,浪迹天涯,我向往的日子是个人挺进世界的纵深;扶老携幼的家族只能是一个负累。待到我踏入中年,定了定神想到了家族的时候,那一幢老宅子已经轰地成为一地的瓦砾。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出版至今的这一段时间里,我的一个叔叔过世。他患了脑瘤,手术之后失明,继而丧失意识,浑浑噩噩地拖了几年之后离开。我的另一个叔叔患了食道癌,已经到了晚期。病痛,衰弱,上一代渐渐老迈、黯淡;家族里的大多数晚辈分散在各自的角落里对付粗砺的日子,几乎不怎么往来。一地瓦砾的生活,这是我想到的一句话。这种生活坚硬,乏味,枯涩,种种多余的温柔、豪爽、亲善、清高都已经拧干。一元钱就是一元钱,一块砖就是一块砖,锱铢必较,越界必究;哪怕是一双袜子,几文小钱,该变脸就变脸,决不碍着什么情面。我们没有万贯家财,也不必因为念了一两本书就在那里发酸。要不是敢于骂街撒泼,周围的人早就踩到脸上来了。
我没有任何异议——我也曾经在这种生活之中打过滚。然而,一个从未谋面的先人就是在这个时刻浮出我的意识:我的太祖父。他从这个城市的郊区闯入,一来二去竟然挣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他是中兴这个家族的大人物。作为长孙,父亲是他的掌上明珠。父亲小时候时常被太祖父带上黄包车一同到轮船公司上班。不仅光宗耀祖,估计太祖父还指望这一份家业庇荫子孙后代。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先人,当年他为自己修建的大坟墓已经预留了父亲母亲的席位。不知他有没有想到,偌大的一份家业散落得如此之快?我猜他在地下肯定清晰地听到,那一幢老宅子轰地坍塌为一地瓦砾。这是不是他挣下的家业里最后一笔财产?从此,他的子孙再也不会聚在自己的屋檐下,交换街谈巷议,家长里短,然后一起吃一盘热气腾腾的年糕。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古人的确有一些不凡的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