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希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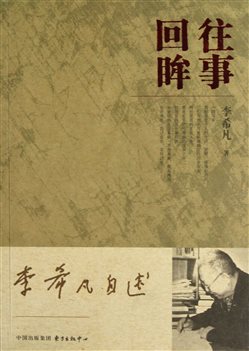
《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李希凡 着 东方出版中心2013.1
1956年,对《人民日报》,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改版,由四个版增加到八个版,各组都扩充了编制。部门名称也改了,文艺组改成了“文学艺术暨副刊部”,下分四个组:评论组、作品组、副刊组、美术组,从社内外调来二十多位编辑,三位部主任林淡秋、袁水拍、华君武。两位副主任,一是田钟洛同志,一为苏光同志。可谓人才济济!我自然在评论组。
报纸7月1日改版,大批人马都在四出约稿,我奉命去上海。上海是近代史上文人聚居之地。我虽是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去上海,但光乔木同志就开出十几位老人、名人的名单,我一位一位地去拜访约稿就是,更重要的是有《人民日报》的金字招牌。我到上海,住在《人民日报》记者站,当时常驻上海的是一对夫妇季音和习平。他们也比我大不了多少,习平可能还要小一点,两个孩子都只有几岁,还有一位老人。至少第一天早餐是他们招待我的。习平同志是个爽快人,我到上海约稿,她给我出了许多好主意。第一天,她就教我先去拜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别露乔木的名单,先请他给你介绍几位作者。你见他就称呼他“春桥同志”,千万别加什么官衔,他不喜欢。我问为什么?习平半开玩笑地说:你看中央领导同志,不是都有特定的称谓嘛——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独少奇没称官衔,全党都称他少奇同志,主席不在,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我表示还是不懂,这时,季音同志已经截住习平的话。说希凡刚来,对上海很生疏,你讲这个干什么!习平嘟囔了一句:我就看不惯他那臭架子。此前,我不知道张春桥是谁,更不会想到未来他“文革”时的“叱咤风云”,但搞宣传的,到地方去先拜访宣传部长,这倒是惯例。我打了个电话,秘书通知我,上午十点春桥同志等我。我准时在他办公室见到了他,无须说明来意,因为全党都已知道《人民日报》要改版,张春桥说,你来上海约稿,无疑是约文艺稿,这里既有老左翼,也有老解放,上海党支持《人民日报》多在上海开展工作,老人、新人都可以约稿,上海很重视培养工人作家、青年文艺工作者,他推荐了姚文元和胡万春。我自然先按照乔木同志的名单,去看望了许多老学者、老报人,如施蛰存、谭正璧、赵景深、傅雷等;也到上海作家协会拜访了吴强、峻青、以群、孔罗荪等同志。有些老先生,还曾是上世纪30年代鲁迅笔下的“论敌”,但他们都是知识渊博之士,这次出差我不是为评论版,是为文艺部,主要是为副刊约稿,因为副刊什么稿件都需要。老先生们都愿意给副刊写稿。我去傅雷先生家约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讲到住处,他的家既不同于雪峰同志在北京的旧式四合院(现在是大杂院),也不是郭老那样的旧王府老宅,而是几间既有红木家具,又有现代书柜、沙发陈设的静静的小院。房间不多,我看到了一架钢琴,我想它就是造就傅聪的那架琴了。傅先生很健谈,不仅熟悉欧美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深。听我说,我和傅聪在华沙使馆有一面之识,我也见到傅夫人和傅聪的弟弟。兄弟二人都像母亲。傅聪是当时留学生中的美男子。母亲很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傅聪在华沙的生活情况,其实,我已回国一年了,哪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何况道听途说的东西,也不能传给他父母呵!只能说,他在波兰很有名,我在联欢节上听了他的演奏,很受欢迎,至于有几位波兰姑娘在追他之类,却没敢透露一点风声。
我在波兰听人谈起傅聪的“音乐教育”,就知道傅先生是位严父,对傅聪也有过棍棒教育,但一看见傅夫人,又知道他有一位温柔文静的慈母。傅先生并没有多问傅聪的情况。我说明来意,特别说明,乔木同志、邓拓同志,希望傅先生给《人民日报》写写文章谈谈文学翻译问题,现在国外文学译得不少,译文好的却少。傅先生说,现在谈这问题有点难处,谈深一点就得举实例,谈实了就要得罪人啦!他认为,译文当然要符合原意,他还认为,如果遇到习俗的用语和成语,最好还能找到和本国含义相同的语言和成语,这样并不损害原文,又能使译文活起来,加强读者的理解。他问我,读过他翻译的书没有,我说:我只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儿》。他笑了,说够多了,这是我大半辈子的工作。我说,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时,年纪不大,有好多读不懂的东西。巴尔扎克的这两本书,我很喜欢读。我最早还读过一位姓高的翻译家译的《欧也妮·葛朗台》,我倒不是当面捧场,高译本确实不如傅译本生动感人,深刻耐读,特别是对老葛朗台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傅先生听了我的看法,倒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看他的译文,注意有什么看不懂的译文原意,记下来告诉他。当我告辞时,三小时已经过去了,傅先生很客气,留我吃饭。我笑着说:我没吃过上海汤包,我已看中了南京路口的汤包店了。傅先生送我出了小院。我不虚此行,1956年到1957年,我曾收到他两篇文章,都发表在评论版上。此后,虽也通过几封信,但也就见过傅雷先生这一面。我这次出差上海,主要是按乔木同志开出的名单去拜访约稿的。约有十数人。1956年创刊后的那段时间老人们写的稿件陆续寄来,也都陆续发表了。
当然,张春桥推荐的几位青年作者,我也都拜访过了。我只约了姚文元和胡万春写稿。胡万春后来成了我的好友,但不知为什么他始终没给我寄过稿子。姚文元我是登门拜访的,那时他虽已有了名气,但也像我一样,不过是《萌芽》的普通编辑。我见他时,上海已是盛夏,他只穿着背心短裤蹲在椅子上,看到我敲门进来,他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自报家门,彼此虽未见过,却已知名。用不着客气,我说明来意。他当然知道《人民日报》要改版,他爱写杂文,也搞评论,我向他约了稿,又请他介绍了一下上海工人作者的情况。大概因为彼此都拙于言辞,谈了一会儿,就无话可说了。他送我出来,我这北方大个儿,总觉得他长得太矮。1956年的副刊上,也发过他一篇杂文,但忘了是什么内容。
在上海出差,我遇到了两大困难:一是语言不通,主要是我听不懂上海人说话;二是走路不辨东西南北。在北京,我有飞鸽牌,骑着它可以满城赶场。上海当时公共汽车也较多,而这个弄,那个弄,我总走错路,好一阵子,才能找到老先生们的家。看起来,能住上傅先生家那样小院的,实在不多,而且一般地说,即使大名人,也往往住得很挤,似是比北京的居住条件还差一些。当时的“洋房”高楼虽比北京多一些,却没有几个文化人能住得上。
来源:《书摘》201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