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志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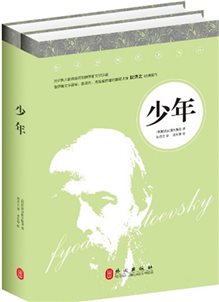
《少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着 外文出版社 2014.1
说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也是世袭贵族,但久已没落,彼得大帝规定,没有业绩的贵族也就不再享有任何权力。后来作家的父亲因为在医院救治贫民有功,获得过官方奖励,晋升八等文官,从而再度获得贵族封号,并在乡下购置了世袭领地。但老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辞去公职,试图经营庄园致富,却因夫人过世,酗酒成性,最后倒毙在乡间的野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幼从他这位“贵族”父亲身上几乎没有得到过父爱的温暖,甚至在军事工程学校上学的时候,还被吝啬的父亲断绝过生活费的供应。也许这就是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困顿中度过,他的成名作就叫《穷人》,而成名不久即因参与政治活动遭流放十年。此后,他办过杂志,赔钱,写作虽然带给了他巨大的声誉,但钱仍然赚不到。
1874年12月20日他在给妻子安娜的信中感叹:“唉,没有一个书商作出反应,看样子《死屋手记》会滞销,除非以后图书馆和个别的爱好者会慢慢地去购买。人家不太器重咱们,安尼娅。昨天我在《公民》上看到,列夫·托尔斯泰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卖给了《俄国导报》,四十印张,从一月份起开始连载——每一印张五百卢布,总共二万卢布。我呢,他们连二百五十卢布都无法马上拍板,反倒心甘情愿地付托尔斯泰五百卢布!他们对我的评价太低了,就因为我卖文为生……不过,哪怕我们明年去讨饭,我也决不会在思想倾向上作出一点让步!”这封信谈的其实不是小说《群魔》,而是他新创作的小说《少年》。当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把《少年》拿给《俄国导报》,但后者却因为要连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而拒绝了他。这封信透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复杂的心态,“我卖文为生”——表明作家对自己身份的某种无奈,没落贵族,没有钱就是普通平民,而托尔斯泰是世袭大贵族,坐拥巨富。虽然到了7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同样可以对俄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如果是一个世袭贵族而兼着名作家,则市场号召力就远远大于一个靠“卖文为生”的文人。尽管如此,作家还是表示他绝不会因此而向作为“市场”代表的杂志屈服。那么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思想倾向”是什么呢?
在我理解,就是他基于自己生命体验而形成的基本倾向,也就是对这种“边缘化”生存价值的探索与肯定。有人认为《少年》的主题是揭示俄罗斯社会的“偶合家庭”现象,我认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理解。其实小说真正的意图就是要表明,一个失去了传统的家庭关爱的漂泊者,是如何完成一桩崇高的精神守护的使命。父亲给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阴影,使得作家一生从不愿意对别人谈起父亲。但这种人生体验却对他的创作起了重要的作用。父爱的缺失,使作家一生都觉得自己像一个漂泊的“少年”,都是在不断逃离、归属中摸索着成长。《少年》的主人公阿尔卡季说穿了不过就是作家本人生活体验的镜像。他从一出生就体验到了生命的悲剧性:私生子,被生父所弃,养父也弃家而去。自他人生的第一个记忆起,他就是一个被遗弃的边缘人。其实,这些都不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自我成长的一种描摹,只是他通过艺术的手段把这种情境戏剧化了。不错,他是在讲故事,但是,正像他年轻时所说的:
“人是一个秘密。应当猜透它,即使你穷毕生之力去猜解它,也不要说虚度了光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做一个人。”那么,这个秘密到底如何?作家思考的其实就是,一个人在被无情地抛到这个充满悖谬性的世界上时,他应当怎样走过自己的生命之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人生面临着两个对立性选择:“神人”还是“人神”。选择“神人”,就是选择基督(基督是由神降为人),放弃世俗利益,走向彻底的精神之路——自我舍弃和牺牲;选择“人神”,就是选择放弃基督,自我成神,从而走上权力和利益追逐之路。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就是在这两种选择的矛盾中走过他的人生道路的。他曾经一方面声称:“我是一个时代的产儿,一个无信仰论和怀疑论的产儿。”一方面又说自己怀疑的激情越高涨,信仰的渴望越强烈。总之,是在对基督的怀疑和信仰之中挣扎。这与其说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不如说是作家特殊的人生体验造成的。当他在失去了家庭之爱,长期被抛到贫困无助的境地的过程中,便可能丧失对信仰的坚定信念,从而认同自我成神的道路——追求物质和社会权力。而这正是少年阿尔卡季在小说中最初的选择。
阿尔卡季在走入社会、最终意识到只有靠他自己的努力才能在世界上立足的时候,他选择了“人神”之路。他下决心要成为罗特希尔德(欧洲金融之父)式的富翁,他想像自己一朝拥有“亿万财产”,内心充满了自豪,却仍然“穿上旧大衣、带着把雨伞步行”,那种情形是何等豪迈!他幻想自己将成为一个外表是普通人,但内心却是一个超越了伽利略、哥白尼、拿破仑的天才!看上去,小说又将重复作家10年前写作《罪与罚》时的主题。当年,比少年阿尔卡季大不了几岁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同样的信念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太,那时,作家本人也许还相信“人神”之恶正在主宰一个时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坚信,只有约伯的道路才是人类最终的选择,也就是从质询走向皈依,从“人神”走向“神人”。所以,在《少年》中,作家没有放任阿尔卡季走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道路,而是在他选择罗特希尔德之路的那一刻起,就给他设定了一个底线,让他带着对自我选择的质疑开始这个选择。所以,少年一边憧憬成为欧洲巨富,一边扪心自问:“难道我的思想禁止我行善吗?难道这种思想对他人有害吗?”其实也就是从这一刻起,阿尔卡季就在不断地推翻自己最初的选择,而一步一步完成着自己的精神之旅。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让这个选择了自我成神的少年对社会充满复仇的欲望,而是在他的灵魂之中置入了一颗神性的种子。因此,每当他试图去恨,最后的结果却是爱;每当他想要去报复,最后的结果却是和解。他在充斥着污秽的环境中就凭着这种先验的神性而成长,父亲遗弃了他,他却一步步打消了对生父的敌意,母亲没有给他应有的爱,却获得了他的温情,他本来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财富梦,但却绝不忍去伤害他人。“难道这一切都是物质的吗,现在世界上的事仅仅要靠金融手段来解决吗?”这句对父亲的提问,其实也是阿尔卡季对自己“罗特希尔德思想”的质疑,少年就在这种质疑中向我们昭示着作家本人要向这个世界敞开的思想。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独白主义者,在小说中阿尔卡季并没有成为像他的养父马卡尔那样的坚定信仰者,这是作家惯用的复调手法。但这种手法的真正意义却往往被我们忽视了,其实,这种手法并不表明作家本人放弃了对不同思想的评判,恰恰相反,他是要在各种强有力的思想——包括他视为大恶的“人神”立场——的交锋中,让世人看到自己切身所处的悖谬性现实,从而像一个成熟的思想者,在自我内心的对话中,像阿尔卡季那样长大、成熟、走向新的生命境界。我想,这也正是《少年》给身处于后现代境况中的我们的启示。
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