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舒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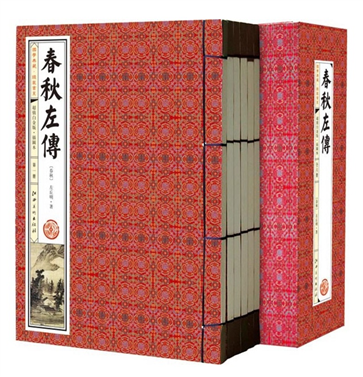
《春秋左传》 [春秋]左丘明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12
最近在周口店附近发现的4万年前的史前人类化石,其体质特征表明东亚的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种并不都是来自非洲的。这个发现对于前些年风行一时的世界各个人种“走出非洲”假说,形成了新的质疑;也给有关中国人种来源的想象带来新的刺激,让人们有理由打破一源说,再次面对多源交融的复杂局面。如果说史前悠远的石器时代人种问题实在不好说,那么就看看略近一些的,如安阳殷墟人口的种族成分,也显示出非常高的多元特征。读李济的《关于殷商人群的体质人类学概述》一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足以了解其大概。若能够再重温一下体质人类学家史禄国先生关于史前中原地区居住的是通古斯人种的观点,就会对远古中国人种来源问题之微妙复杂的情况,有更丰富的体会。
若要追溯人种来源复杂性在历史上被遮蔽的原因,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因于大一统的思维定式,以及建立在这种思维定式上的正统历史观。而要找出对形成中国古代正统历史观具有奠基作用的一部书,那就是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
历史与偏见
由于历史通常指成文历史,因而学界总是把文字系统的有无看成一种界标:有文字记载,则为历史时期,或叫“文明史”;文字出现之前,通称“史前期”或“史前时代”。若相对“文明”而言,则称“蒙昧时代”。与文字大约同时出现的金属冶炼也被视为文明成立的要素之一。所以史前期与历史时期的分界又可以表述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或“铜器时代”)。
我们通常说的“中国历史”,是以王朝正史的权力话语系统为核心而建构和世代传袭的一套皇家中心的断代和编年叙事。这样的一套以汉字为载体的叙事系统,无疑属于古代封建王权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必然要反复强调、张扬和突出某些中心性的东西,同时也要有意地蔑视、压抑、回避、遮蔽许多边缘性的东西。史家记录这个而不记录那个,这种取舍之间的学问非常深奥渊博,但却不是通常所说的客观的历史知识问题,而是一种主观的文化政治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读史要首先注意的。
没有这种自觉的意识,往往就会不自觉地认同中央王朝权力话语,站到正统立场上去看待史书叙事的问题。其结果是被这套权力话语的叙事所瞒和骗,而不自知。
史书的政治倾向又可以围绕历史主体的身份-文化认同,细分为族群划界,阶级和阶层的划界,性别划界这三大层面。由此而形成清晰可辨的社会等级秩序,其功能在于明确叙事者的取舍原则与褒贬好恶原则:亲疏内外尊卑。古代史家的所谓“通古今之变”,无非是寻找一代代王朝兴亡成败的道理,给后代的统治者以史的经验和鉴戒。《资治通鉴》这部着名的通史之书就得名于此。这样一来,凡是代表着新政权兴起的一方,就必然备受推崇而百般美化,如周武王、汉高祖、唐太宗等。而那些不幸处于王朝权力衰落和覆灭时期的王者,几乎没有例外被叙述为道德和智力的双重缺陷者,即通常所谓昏君暴君,如夏桀、殷纣、周幽王等。如果在权力兴衰的叙事中要突出历史因果的所谓规则,那么往往会有附加的父权制性别偏见所主宰的两性叙事――从妹喜迷惑夏桀,到妲己惑殷纣,乃至褒姒的戏烽火,杨贵妃的回眸一笑等等,总之一句话:美色误国,女人祸水。
再比如,同样是一“国”的历史,鲁国的史书《春秋》,叙事历二百多年,被奉为儒家至上经典,成为百代的兴废之鉴。而西夏王国近二百年的历史,却被中央王朝的正面叙事几乎全然忽略到边缘去了!为什么如此地厚此薄彼呢?答案可以非常简单:西夏一方是皇家史书正面叙事的空白,就因为是非我族类的党项人,是相对于中央王朝权力的边缘和异己者,乃至敌对者。鲁国一方是正统,从左丘明作《左传》到董仲舒作《繁露》,一部《春秋》已经获得非同寻常的文化政治意蕴。
历史:从“吃人”到“瞒骗”
同样,与西周王朝并存于关中西部山区的“弓鱼”国,在流传至今的历史书写中也没有一个字的记载,好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样!二十世纪以来在宝鸡地区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铭文,才让世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与周王朝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八十年代四川广汉新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新世纪伊始成都发掘出的金沙遗址,其青铜大立人造型高达2米62,其祭祀用的象牙数以吨计,这些都是中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情形,而中原中心的历史叙事却从来没有记载。换言之,这些中国境内的伟大文明全都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王朝历史叙事中只字未提的!如果不是大量珍贵文物重见天日,后代人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曾经在巴蜀灿烂辉煌的古老文化。如此看来,我们不得不在新的考古事实的一再启发之下开始觉悟: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一部成文的“中国历史”,其实倒不像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借狂人之口所说的那样严重――“吃人”,而是瞒人和骗人。它在从人文初祖黄帝到清朝末代皇帝的五千年选择叙事中,看似完整周全,举世无双,但其实不知道瞒下了多少历史真相,骗过了多少代天真虔诚的文字历史信奉者。难怪古今人异口同声地说:人生识字糊涂始。我们过去只知道文字是表达和叙事的工具,原来文字也是权力对大众实施瞒和骗的最有效工具。对于盲从所谓文字记载的信众来说,其效果尤其明显。
如果要追究一下在正统史观压制之下被“中国历史”所遮蔽所遗忘的主要原因,答案简单的惊人:就因为不属于“中国”。
那么,这一套以“中国”为核心表象的写史思路究竟是怎样由来的?谁才是被历史叙述者所一致推崇的“中国”呢?原来就是相对于四方的蛮夷戎狄等被贬抑、被边缘化和妖魔化的少数族群而言的中原政权。
《春秋》与“中国”的文化政治
古汉语中的“中国”一词与现代汉语中的“中国”一词是很不相同的。由于上古的“国”往往仅用于指方国或部落联盟,“中国”也就仅仅相当于想象中位于地理中央的一个地区,接近于后来所说的“中原”一带。所以按照“五岳”的东西南北中五方位地理空间模式,以位于河南西部的中岳嵩山为中心的秦、晋南、豫一带地区,是历来的皇权话语所公认的“中国”。从行政区划的地理意义之“中国”,到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一个约定俗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就是由东周时期的鲁国史书《春秋》开始建构的。
《春秋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这里的“中国”与“夷狄”相对而言,可知当时的文化认同问题之核心内涵。
不过,《春秋》作者判断是夷狄还是中国的标准,可以不必拘泥于种族和地域,而是以西周王朝所确立的正统之“礼”为尺度。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政治的尺度。如果人种上的夷狄采用了中国之礼,也可视之为中国,为君子。反之亦然,人种上地理上的中国若不用中国之礼,也可视为夷狄,为小人。这种不用唯一固定的标准来机械划分华夷界限的书写策略,被董仲舒称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揭示出非常重要的文化政治修辞学的微妙之处。
清代儒者苏舆列举历代儒者对此种文化政治修辞术的体悟和解说,非常精当:
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程子亦云:“《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道,即夷之。”是故卫而戎焉(隐七年),邾娄、牟葛(桓十五年)、郑、晋(昭三年)而狄焉。既内而我鲁,亦以城邾娄葭而狄焉(哀六年)以此见中国夷狄之判,圣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然《春秋》于中国、大夷、小夷,各有名伦,不相假借,抑又谨于华夷之防。董子两明其义。宋胡安国诸人,以为《春秋》专重攘夷,固因时之论,得其一端耳。(《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6~47页)
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春秋》及三传的开端结尾,对正统的历史时间观也会有所体会。《春秋》叙事开始于“元年春王正月”。比较神话学告诉我们,这样的写法是要重新模拟创世神话的叙事法则,突出新的时间周期的开辟意蕴。《公羊》叙事终于获麟;而《左传》叙事终于孔丘卒,按照弗莱的原型理论,圣物的展现和主人公之死,都属于所谓“秋天的神话”。
为什么《左传》的地位高于其它,因为是“素王”孔子之“素臣”左丘明是独家正宗嫡传。所谓素王指的是,没有王位却有王之德的人。“素王之文”说的产生并不是在孔子和左丘明的春秋时代,而是肇端于战国时代的孟子,完成在汉代,目的是给在王位上的汉代统治者建立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提供历史权威的基础。“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左传序》)“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章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这里被“绌”的夏,指的就是中原以西地区的民族,即以氐羌为主体的游牧文化群落。在上古语境中,说“夏”还是相当尊敬的,因为毕竟与“华”相去不远。二者合成词“华夏”,几乎是“中国”的同义词。更为直截了当的蔑称则是夷狄、戎狄、姜戎、西戎一类。由于明确提出的“亲周”缘故,凡是被周人视为夷狄的,那就很难改变被正统所歧视的身份,除非表示出“宗周”的归顺行为。
《公羊春秋》在西汉获得独大的地位不是偶然的,而是它兼传微言和大义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皮锡瑞《经学通论》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唯《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谵,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皮氏对三传各自特色的区分和把握,确实具有远见卓识。如果今人能够从文化政治的新视角对“微言”与“大义”的构成底蕴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将能够清楚地透视出从“经”到“传”的文化价值再建构过程。
《春秋》的神话模式
《春秋》虽为史书之祖,儒家六经之一,但是其叙事结构背后却有支配性的神话模式。而具体的神话情节也时有显现,为“想象的地理”或“想象的共同体”提供核心的原型意象。其由来十分久远了。我们在《论语》中就已经看到神话意象如何出现在孔子的想象之中。如《子罕》篇的感叹辞:“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凤鸟与四方风神的相互认同性质,已经从甲骨文和《山海经》得到证明。而风神又被神话想象成至高天帝的使者,甲骨卜辞谓“帝使凤”,说的就是这种神话观念。《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所见内圆外方的玉琮,从史前时代到夏商周老三代,春秋战国和汉代新三代,代代相承,体现着此种“中央天帝通过四凤鸟而统治四方”的神权政治蕴涵。特别是几个四面浮雕凤鸟的玉琮,更是形象直观地展现神话观的生动物证。注家云:“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王者的符号权威来自中央与四方的空间关系。《论语》多处表明了王者的“四方”的意识。哪怕是“素王”,也同样具有中央政治神话想象的巨大魄力吧。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就是一个明证。《春秋》这样突出“中国”想象的史书被归到孔圣人名下,绝非偶然。
来源:《博览群书》2007年第8期